外卖大战1元订单频现 小店月亏八万陪跑

资料图。源自视觉中国
摘要:
一块钱能买到三串土豆片和七瓶矿泉水,这样的订单多次出现在餐饮老板王宏的手机上,“被薅羊毛到这种地步”,他感到匪夷所思。外卖大战中,餐饮店主们的牢骚发不完。
补贴砸下去,“羊毛”却出在“狗”身上,门店营业额被注水,变成无法参考的指标。价格作为交易核心,被平台补贴叠上一层又一层中间差,商家和消费者作为真正的交易双方,却无法直观感受到,谁出了多少钱,谁收了多少钱。
平台在打补贴战,小店在打利润保卫战,胜者属于能玩得明白流量的人。有商家发现,即便是在这个规则变得更加复杂的线上空间里,单量、流量仍然比利润更重要。
文|解亦鸿
编辑|陶若谷
小店没的选
王宏在深圳开过三家钵钵鸡店,倒了两家,还剩一家。今年五月,深圳龙岗一条商业街上,一家牛肉火锅倒闭了。他盘下铺子,选了个“良辰吉日”——5月25号,新店开业。
第一个月净亏八万,王宏起初没把这个数字和“外卖大战”关联上。新店需要从头积累客源,买流量,买达人推广,都要成本,前期赔钱是正常的。
到了七月初,他像往常一样查看新订单,发现顾客只花一块钱,就买了三串土豆片和七瓶矿泉水。没过一会儿,同一地址、不同手机号,又来了两笔一模一样的订单。“被薅羊毛到这种地步”,王宏感到匪夷所思,“超市里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水。”后来他在新闻里看到,一家平台又冲锋了,宣布补贴500亿。他才意识到,开店时机选得太烂了。
平台补贴的力度有多大?
4月,骑手争夺战全面升级后,京东宣布上线“百亿补贴”。饿了么在4月末以“百亿补贴”参战,很快正式并入阿里集团。5月下旬,阿里宣布其外卖单日订单量突破4000万单。紧接着,美团在财报会上表态,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赢得比赛”。
对钵钵鸡这样的小生意来说,营业额变成一个无法参考的指标,看似很高,实际不赚钱。王宏收到过一笔营业额为30块钱的订单,膨胀红包减7块,新店立减1块,平台抽佣6%,再参加免配送费活动,配送费减6块,商家到手不到15块钱。而小生意的毛利率通常只有50%。王宏最烦遇到“膨胀红包”,“膨胀之后,一单的毛利只有几毛钱。”
展开全文
补贴砸下去,客单价直接腰斩。王宏的小店,外卖订单在六月、七月一直涨,利润却在下降,“出餐没停过,但是全拿去陪平台搞补贴活动。”这是多位餐饮老板的感受。
武汉南京路,一家楚菜中餐店的老板在新来的外卖订单上看到,一张18块钱的优惠券,平台和商家各承担9块,她吐槽说,“大厂砸500亿,难道要让餐饮界陪跑一半?”
《冰点周刊》报道,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针对外卖大战调研了33家商户,涉及超市、便利店、餐饮企业。协会发现,商家所承担比例不尽相同,多数为30%-70%,少数承担补贴份额超过70%。
补贴力度最大的是奶茶咖啡。一位顾客调侃自己“点了一杯取不到的奶茶”——下单后等了一个小时,骑手仍然没取餐,半小时后她私信催促,骑手回复:没办法,现在站点人均20多单起步。又等半个小时,她自己也佛系了,“反正只花了3块钱。”
7月12日晚上10点,南昌一家蜜雪冰城柜台上还剩近30杯无人认领的饮料。据江南都市报报道,顾客在线上点单后没来自提,没人领的奶茶被店员扔进垃圾桶,店长告诉记者,上周也扔了二三十杯。
爆单造成了外卖骑手的挤兑、拥堵。七月,深圳刮起了台风,送餐的骑手更少了。做钵钵鸡的王宏,餐做好了却没人来送,最终顾客等不及,取消订单。他给外卖平台打电话申诉。业务员告诉他,赔付规则按照“订单完成率”来定:完成率高于98%时,平台可以赔付;低于98%不再赔付。
王宏讲述,自己一头雾水,“完成率是什么意思?以前都没听说过。”业务员解释完,他听明白了,每100单平台最多赔两单,超出部分不赔。7月20号这天,像这样的取消订单,他一共碰到了28单。

蜜雪冰城爆单。源自视觉中国
外卖小票的显示信息也有变化:最直观显示的只有橙色粗体的“预计收入”,即扣除商家对顾客的活动补贴、平台佣金、配送服务费之后的金额。橙字下方,一行灰色小字写着“顾客实际支付”,点开旁边的右箭头,才能看到被折叠的具体数字。
在王宏看来,价格是交易的核心,也是买卖双方博弈的结果。商家知道顾客付了多少钱,顾客知道商家收了多少钱,当双方对价值的认知存在“互利差空间”,进而通过价格博弈实现各自利益的交换,交易才可能发生。“否则,商家钱收少了,顾客却埋怨商家,为什么只给我提供这样的服务?”他的牢骚发不完。
他的理想状态是外卖与堂食营业额达到1:1的比例——堂食利润高,老板们普遍喜欢堂食订单,王宏的店铺,每月三万五的房租水电成本,他觉得只做外卖太亏了,但现实的比例是外卖远超堂食,达到3:1。
面对外卖大战的冲击,一些连锁品牌的餐饮老板开始设定红线,要求严格控制外卖订单占比,一旦超过红线,店长会被直接问责。但在王宏这样的店主看来,“小店没的选。大品牌才会去算挣多还是挣少,我不懂怎么控制,只希望单子越来越多。不过,没钱挣的单子最好别来。”
7天定生死,退出的白鸽
客单价持续走低,但不做外卖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6月26号,鞍山一个钢厂家属院里,27岁的白颖在楼下开了一间东北饭包店。店面不大,主要服务小区熟客。试运营一周积累了一些回头客,不怎么赚钱。看到竞争对手基本都在做外卖,7月2号,白颖也入驻了一家外卖平台。
当月,市场监管总局约谈京东、美团、饿了么等企业,强调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。但平台还在冲单,外卖大战持续升温。
白颖注册当天,几十个代运营人员找上门,手机里电话不断,有声称是平台官方的,也有称第三方的。她不知道哪个靠谱,最后选了美团业务经理介绍来的朋友,认为虽然是第三方,但也是平台官方业务员的人脉,信得过。代运营告诉白颖,外卖店和自媒体一样,需要“起号”,新店期至关重要,“可以帮你把单量冲起来,否则后续除了回头客,很难有新客。”
代运营接手后,为她优化了菜品图片和文字描述:鸡蛋酱饭包是“满满的烟火气”,香菇酱饭包“越嚼越有滋味儿”,猪肉酱饭包后面写上“老东北味儿”。包装完成,白颖的店铺参加了平台的新店优惠活动,并开通了“霸王餐”活动——请顾客免费吃换取好评。
一份“满满的烟火气鸡蛋酱饭包”订单,小票显示预计收入不到堂食价的一半。她查看后台信息,发现顾客实际只付了8毛——除去平台抽佣,还有新客立减、收藏有礼、大额膨胀券等各种新店优惠补贴。白颖看不懂规则,想关掉活动,但代运营提醒她,新店阶段必须参加,否则平台不给推流,单量冲不起来。
从代运营那里,白颖学到了“外卖7天定生死”的规则。第一天完成5单,点亮评分。第二天15-20单,提升转化率。第三天是关键冲刺,目标40-60单。往后几天按1.2至1.5倍稳定增长。
为了完成计划,代运营为她制定了擦边违规的“刷单”策略。白颖让朋友下单点饭包,外卖小哥取餐时,她不出餐,只在袋子里装一瓶矿泉水。她解释,“商家刷单只是为了做数据,不用出餐,就让小哥出去空转一圈。”
但店铺还是没做起来,代运营接连换了两个。白颖不懂其中门道,边做边学,上网搜经验帖,越看越慌——普遍观点是:新店第一个月没起势,后期只会越来越难。
面对不断压缩的利润空间,一些商家选择退出平台的补贴活动。
25岁的霍安是其中之一,他在成都郊区经营一家中餐外卖店。七月第一周,店铺从利润率20%降至10%。到了下旬,店铺有一天的实际收入显示为“负3毛7”,他意识到,必须坚决抵制羊毛党。
霍安在后台撤销了店铺参与的两项补贴活动。一项是自5月31号开始的“下沉城商”优惠券,规则为顾客可使用“天天必膨18元”红包,一个商家每天最多可被使用红包50单,每单商家承担12元,平台承担6元。
另一项是“神抢手”券,可理解为将外卖商品变成团购券,通过“到店自取”或“外卖配送”两种方式完成核销,实现补贴效率最大化。撤销活动第二天,他收到平台业务经理消息,“亲,神抢手活动怎么又取消了?”经理劝他加回来,被霍安拒绝。
七月底,霍安又收到了羊毛党订单,他才发现,自己的店铺重新参加了“神抢手”。他打电话给业务经理直接开骂,“再偷偷给我上活动我就去告你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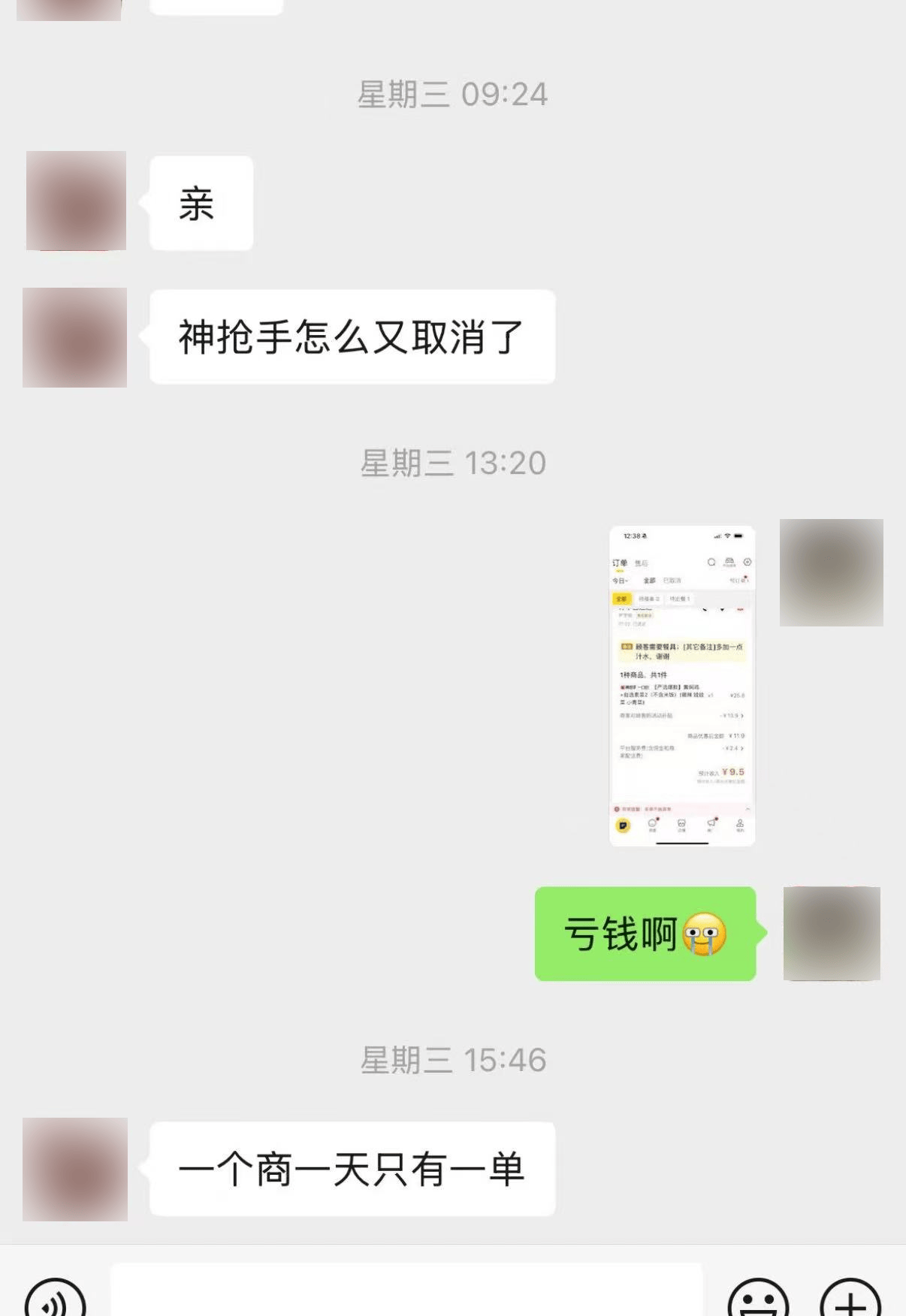
霍安和业务经理的聊天截图
据虎嗅报道,被迫应战的美团在复盘时,认为“自提外卖”和“0元购”两个打法是实现1.5亿订单、守住行业第一的有效动作;为了保住即时零售市场份额(含外卖)第一、订单量第一,部分人员和部门有相应OKR类指标。
一位餐饮公司创始人发现,门店被“自动”开通了另一平台类似“0元购”的活动,他多次与业务员联系,对方回复“有业绩压力”。8月1日,三家平台联合发布声明,承诺停止极端补贴活动。
在武汉烧烤店主季涛看来,不管平台怎么打,商家撤销活动的做法算是另类选择——不参加18元红包,不仅平台会降低推流权重,“顾客也会淘汰你,因为别家更便宜,相当于大家都是乌鸦,只有你去当一只白鸽”。
乌鸦也有聪明的做法。季涛的策略是,通过抬高菜品定价来保障利润——堂食价加上平台抽佣、配送费以及各项活动补贴,“相当于把堂食价提高30%。”
羊毛出在“狗”身上,“猪”来买单
对许多商家来说,外卖大战的核心问题变成,究竟是要单量,还是要每一单的利润?
40岁的上海人周春晓,和丈夫在浦东经营一家本帮面馆。本帮面馆集中在浦西,周春晓抓住这个卖点,“浦东居民不必过江就能吃地道的本帮面。”
面条容易坨,一向不是理想的外卖品类,周春晓的店也以堂食为主,七月初,她才在面馆里真实感受到外卖大战的冲击。附近的白领不再像往常一样到店吃午饭,曾经能翻台坐满三轮的午市,现在一轮之后就渐渐冷清,让她有了危机感。
但周春晓没有撤销任何平台活动,经验告诉她,必须“顺从平台”。
开面馆之前,她和丈夫从寿司店起步,后来加盟炸鸡品牌,做了四年纯外卖店。凭借这段经历,她自诩“把流量玩得非常明白”,第一反应是把外卖定价上调了五到七块。这是她刚上外卖平台时,业务经理教的策略——“外卖定价必须比堂食要高”。这样一来,堂食的本帮炒面18块一盘,调整定价后,在百亿补贴期间,顾客用完神券,不加配送费,外卖点一份仍然是20块。

资料图。源自视觉中国
要利润就意味着抬价,这是季涛的策略。去年夏天,他从武汉一家互联网大厂辞职,目睹了大龄同事被优化,产生年龄焦虑。赶在35岁之前辞职创业开餐饮,是他给自己攒的一个退路。
投入十几万后,季涛在二七路开了烧烤店。起初并不打算做外卖,他认为烧烤讲究现烤现吃,“打包一闷,口感和味道直接打折”。猪肉串和牛肉串都不放孜然,主打食材新鲜,减少烟雾,目标是吸引家庭客群。但八个月下来,成本收不回来,迫于经营压力,今年四月他决定入驻外卖平台。
但80%的外卖订单,实际是将线下老顾客转移到了线上。季涛介绍,老顾客们觉得线上点更便宜,有补贴。六月,堂食营业额下滑到两万,为了维系老顾客,他挨个发微信问候“最近工作怎么样”,再邀请对方来店里。但是到了七月,堂食营业额跌到一万五以下。
季涛尝试拉新自救,出镜拍抖音,用“冇得科技和狠活”为卖点推广团购券,还买了投流推广——他判断抖音不会下场参与外卖大战。但新问题来了,团购券到店量很低,核销率只有5%到8%,相当于顾客买完券,不来店里吃,到期后又把券退掉。
“补贴战意味着,顾客只知道薅平台的羊毛,却不知道羊毛出在狗身上。”在季涛看来,商家抬价是一种自救策略,将平台补贴带来的负担转移到顾客头上,“最后还是猪来买单。”
这原本是互联网经济中一种常见的商业模式,不再直接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带来盈利,而是通过平台服务吸引用户参与,进而从其他渠道获利。放到外卖大战的语境里,“羊毛”代表利润,“狗”是参与者,也就是餐饮商家,季涛解释。
精明的商家会抬高定价,将平台从商家这里扣除的高额补贴,转嫁一部分给顾客承担。顾客薅到的“羊毛”变少,且长远来看,有了单量,培养出消费习惯,实际利润还是出自顾客。
外卖大战之前,就有商家利用平台补贴设计促销活动,主动抬高单量。外卖大战中,商家被迫承担补贴成本,单量同样上涨,但利润空间被挤压,因此需要做出更多取舍。据新识·研究所报道,北京一家做大馅饺子的餐饮店,在外卖大战补贴砸下去之后,从外卖平台全线下线,老板说,“门店承担不起补贴,不如好好做来店里吃饭的客户”。
在上海开面馆的周春晓算了一笔账:客人点单时,如果只点一份面,基本不赚钱;但加一份炸猪排,炸猪排就能带来利润。参加活动,虽然面条不赚钱,但能赚到炸猪排的钱;如果不参加,连炸猪排的钱也赚不到了。
如果撤销活动导致单量下降,等到外卖大战结束,以前累积的漂亮数据也很难恢复。“顾客是闭眼玩家,不知道单量是商家氪金出来的,还是靠菜品实力赢得的,绝大多数只看单量下单。”这是周春晓的经验。
一天晚上收摊下班,她准备去附近吃顿烧烤宵夜,突然意识到,“为什么有羊毛不薅?20多块钱的东西,点外卖到手就几块钱。”她放弃了堂食,回家点外卖。
(应讲述者要求,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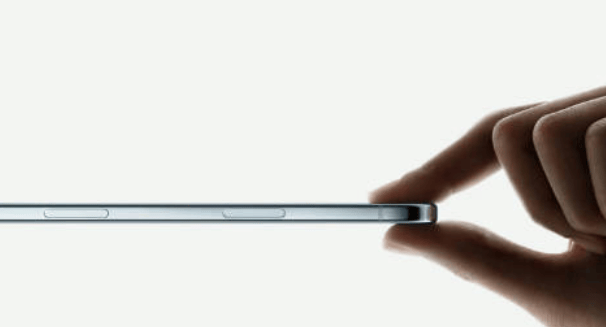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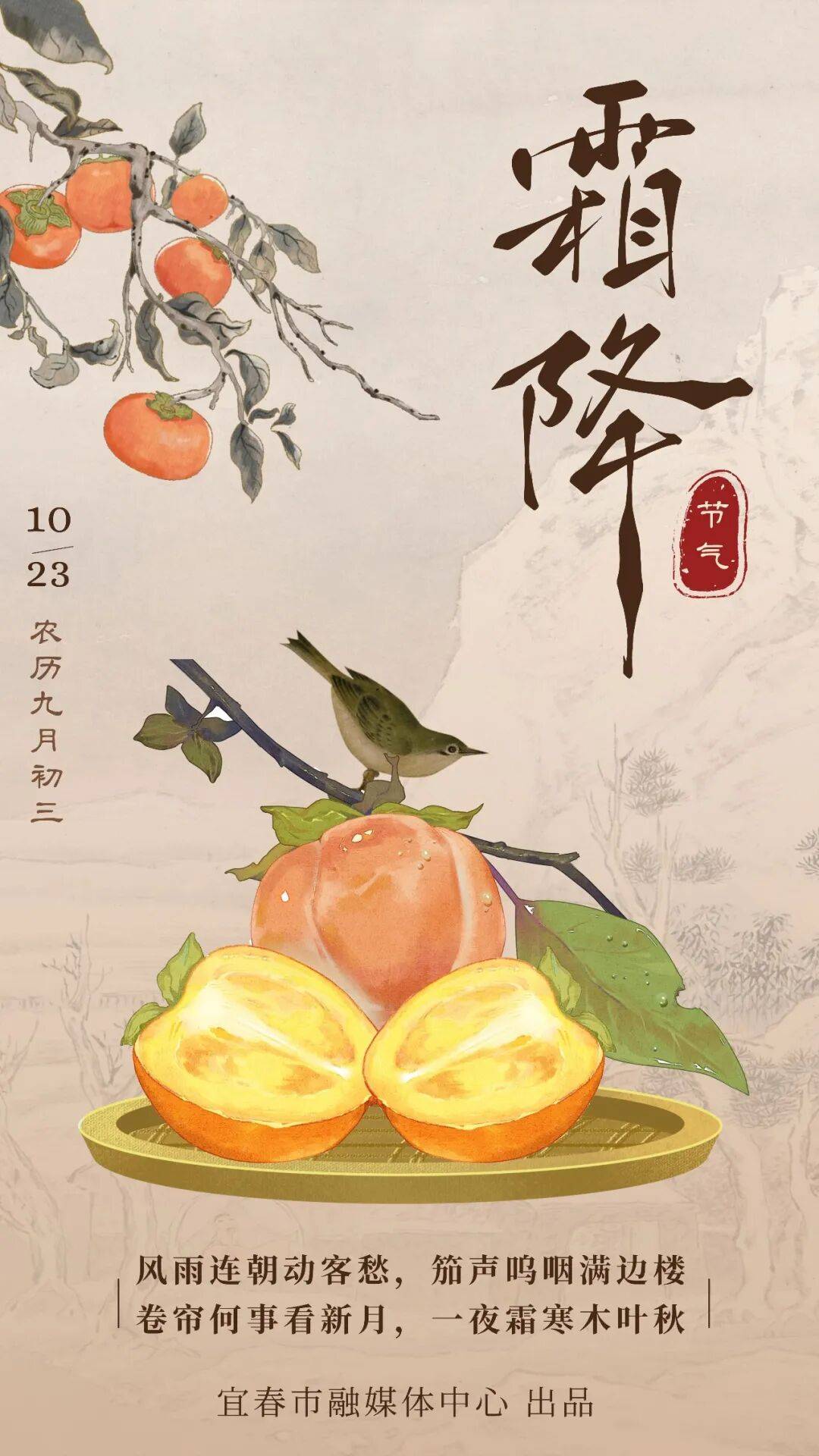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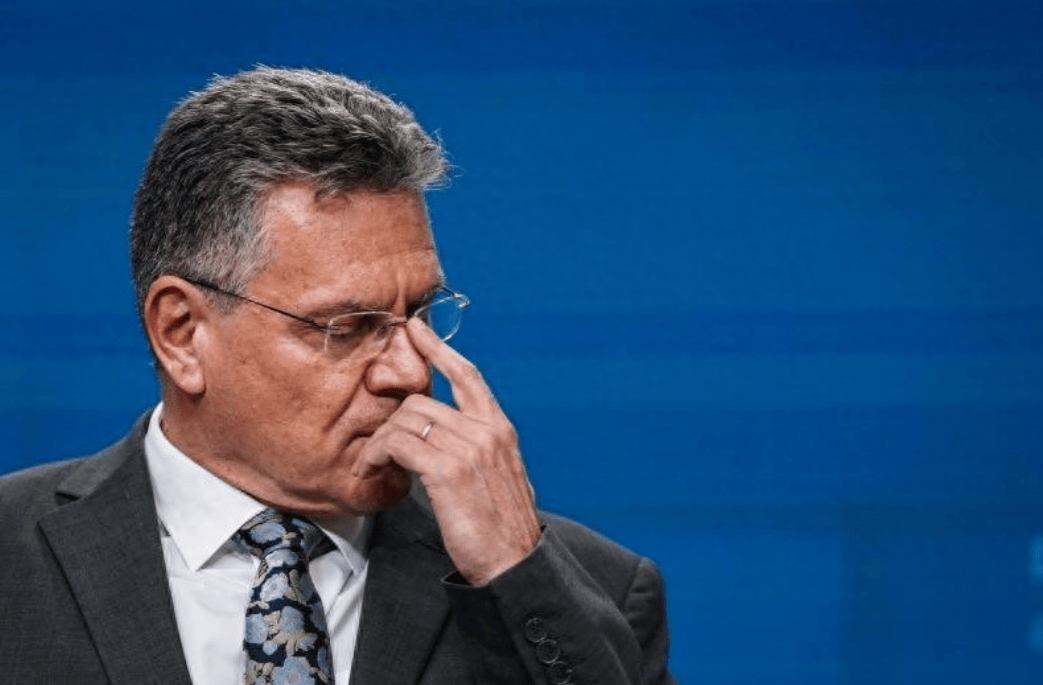
评论